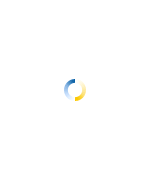播放地址
 《波奇亞》劇情內容介紹
《波奇亞》劇情內容介紹
對一位教皇的血腥時代的描繪。亞歷山大六世是歷史上最臭名昭著,最惡毒最荒淫的教皇之一。他的兒子凱撒是個野心勃勃的極權主義者,極端殘忍冷酷,不擇手段,一心想用暴力統治意大利甚至周邊國家。
幕后故事
文藝復興是這樣一個時代,每個人的欲望都光芒萬丈,每個人的意志都擺在他自己的寶座上。人類成為宇宙的立法者,開始分不清偉大與邪惡的區別。城邦的榮耀、民族國家的偶像,一座座肉體的豐碑,使臺伯河畔那個古老的帝國夢,從墮落的羅馬教會中脫穎而出,像惡之花一樣盛開。
關于文藝復興時期那些“壞得不能再壞”的教皇,電影史上很少有他們的傳記。只有1965年好萊塢的《痛苦與狂喜》,描寫尤利烏斯二世,這個有三個私生子的教皇,邀請米開朗基羅創作了不朽的巨幅穹頂畫《創世紀》和《最后審判》。新教改革前的羅馬,仿佛回到了二千年前諸神狂歡的世代。一面是荒淫、墮落和層出不窮的陰謀,一面是散發著肉體氣息的偉大藝術。教皇和紅衣主教們,幾乎人人都包養情婦,生養眾多。在整個十五世紀,沒有一個教皇不是通過買賣圣職賄選而來的。除了腐敗的軀殼和堂皇的圣殿,基督信仰在意大利已蕩然無存。一個文藝復興的世界對主教們的淫亂和邪惡,懷著一種寬厚的、甚至如釋重負的好感。而這一系列被稱為“最文藝復興”的教皇們,也無不是藝術的鑒賞者和最慷慨的贊助人。差不多一個世紀,主教們在兩個世界之間猶豫不決,到底是成為凱撒的繼承人,還是繼續做使徒彼得的繼承人?
直到1492年,羅德里格·博爾吉亞當選為教皇。這是出自西班牙裔的博爾吉亞(波奇亞)家族的第二位教皇。他賄賂每一位紅衣主教的巨款,使這位羅馬城最富有的人也差點破產。他以“亞歷山大大帝”為名,稱為亞歷山大六世。他終其一生,扶持四個私生子建立了龐大的權勢。其中一個,紅衣主教凱撒·博爾吉亞,以他的野蠻、殘忍和征戰的天才,在28歲時就為他父親打下了半個意大利,將一個教皇國的夢想獻給他的家族。也成為意大利和羅馬尼亞最令人生畏的統治者。這一對父子的名字,“亞歷山大和凱撒”,仿佛一個咒語,預示著這個世界接下來一個幾百年的噩夢——“凱撒的物歸給凱撒,上帝的物也歸給凱撒”。從此國家主義的光榮與夢想,一直持續到兩次世界大戰及1989年,才算告一段落。
從某個角度說,人類史上沒有比亞歷山大六世更邪惡的統治者。另一位比他好不到那里去的利奧十世,這樣評價他的前任,“我們被世上最野蠻的惡狼抓住了,我們或者逃跑,或者被他生吞活剝”。這位教皇妄稱上帝的名,以最圣潔的外貌施行最污穢的統治。去年以來,西班牙和好萊塢竟不約而同地,接連拍出兩部關于這個家族的傳記片。好萊塢的那部由柯林·法瑞爾主演,尚未公映。我看了西班牙的版本,生怕好萊塢也不會拍得更好了。看這部電影,你會更理解二十年后的新教改革,上帝在那個時代如何呼召他的門徒,扭轉了一個徹底敗壞的歐洲。你也會更加認同,馬丁·路德對著圣彼得大教堂的那個寶座所發出的詛咒,一點也不惡毒,而是對事實的描述——坐在那上面的,是撒旦在人間的代表。
很遺憾的,是電影中沒有出現兩個應該出現的人,一個是畫家達芬奇,他是凱撒軍隊的總工程師,為愷撒設計了可裝載三百多士兵的攻城器械。一個是馬基雅維利,他長期駐在博爾吉亞的宮廷里,在《君主論》里,他將這位被無數歷史學家視為尼祿、卡里古拉一般的暴君的公爵,當作理想君主的典范。馬基雅維利期望這對父子能夠統一意大利,恢復亞歷山大后裔的輝煌。他稱這位不擇手段的公爵是“全意大利最勇敢最聰明的人”。
一個教皇,一個公爵,如果再加一個藝術家和一個政治學者,一幅文藝復興時期的圖畫就更加完整了。失去了與文藝復興的聯系,這些“文藝復興教皇”的道德淪喪與政治權術,就被電影簡化了,成了我們熟悉的宮廷血腥與厚黑學,只不過從我們熟悉的皇宮,換成了我們不熟悉的教廷。
 猜你喜歡
猜你喜歡
-
8.0分10.0分